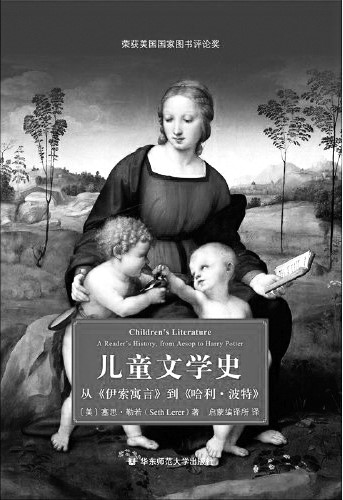
编者按
《伊索寓言》为何从古典时期直至当代都备受推崇?几个世纪前,童书是如何影响孩子的性别观的?男孩的冒险故事为何从岛屿移至帝国,从军队中寻找他们的英雄气概?从《伊索寓言》到《鲁滨孙漂流记》,从《绿山墙的安妮》到《哈利·波特》,塞思·勒若在《儿童文学史——从<伊索寓言>到<哈利·波特>》中为读者梳理了一段从古希腊到近现代的儿童文学史。
在《儿童文学史——从<伊索寓言>到<哈利·波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中,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教授塞思·勒若勾勒了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复杂体系,其社会和美学价值是如何由制作、营销和读者决定的。勒若是一位语言学家,曾任教于普林斯顿与斯坦福大学,他的学术生涯早期专注于中世纪史研究,而后期转向了对儿童文学的关注,这种变化在他看来并不突兀。他认为,儿童文学同时代紧密相连,它的历史也是教育、文化与商业的历史。当我们谈论儿童文学时,除了着眼于一个个富有想象力的故事本身,还需要思考,不同时代的儿童文学承担着什么样的不同的职责?儿童是如何由他们所阅读的书塑造的?儿童文学又是如何被评奖机制形塑与影响的?
文学要培养什么样的儿童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教育将公共生活定为首要目标,因此演说与命令成为儿童教育的重点。孩子们阅读《伊利亚特》和《埃涅阿斯纪》中的选段,以此模仿英雄的成年生活。这些故事关乎权力与控制,同地位、阶级、出身息息相关。它们告诫儿童安分守己,不要僭越,同时成为一个高贵的领导者。这一时期,学会如何命令奴隶也是儿童教育的重点。他们模仿大人下命令,学着成为一个掌控者,一个成年人的雏形。
勒若认为,儿童文学开始成为一个崭新而独立的文学类型在17世纪。受清教徒的家庭观念与对后代的热情的影响,童书受到了重视。清教认为书籍可以塑造生命,只有通过阅读,通过教理回答以及学习典范故事,儿童才能进入天堂。阅读、识别字母和正确解读文字成为教育的核心。这推动了研究字母的散文类型,这些作品对典型的职业、社会规范和道德类型进行概述。托拜厄斯·埃利斯的《英语教学》便是如此。
字母教育书似乎离现代意义上的童书相差甚远。现代社会以动物及物品为主角的拟人故事童书实际上在18世纪晚期才开始流行,而这归功于洛克的哲学思想。勒若描绘了洛克作为一个热情的孩童教育者与儿童文学的种种联系。他曾提出儿童文学的任务是让人理解各种事物,并开始强调感官经验特殊性。这样的观念影响很大,儿童教育因而开始转移到对情感能力的关注。新的文学类型——无生命物的虚构传记,就这样紧随洛克的作品而产生。笔、硬币、玩具,马车成为了小说的主角,宠物开始成为自己传记的叙述者。
洛克在倡导儿童感情培养的同时也强调了个性发展,他反对普遍性,强调特殊性,这也影响了许多儿童文学的写作。这些童书让孩子们开始发展自己的个性,而非按照清教字母教育概括的人的类型模板生活。
童书如何塑造女孩
性别教育童书在当下已经慢慢普及。而在几个世纪前,童书是如何影响孩子的性别观的?在最早期的儿童文学即《伊索寓言》和《格林童话》中,女孩通常作为性欲或嘲笑的对象出现。她们身体与意志薄弱,不是迷路就是受到威胁,有她们出现的文本常充斥着色情意味。《伊索寓言》甚至描述了一个父亲爱上了自己女儿的故事。到了19世纪末,女孩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年轻女人开始上学、上班、旅游、阅读和写作,因为食物质量和卫生条件的提高,女孩的月经初潮提早了,而婚嫁的年龄则提高了。这样的变化让少女时期成为一个人生阶段的专门概念被划分出来。
在此之后,出现了许多描绘少女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与对男孩的冒险故事所呈现的戏剧性描述不同,书中描绘的女孩往往在“专注性”和“剧场性”两种状态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专注性指女孩不直接面对观众的凝视,她们独自看书,照料父母,抚养孩子,这时她们的眼睛低垂。而剧场性则往往充斥于“男孩文学”,他们以正面示人,表现出舞台式的夸张姿态。剧院曾被大多清教徒认为是罪恶的场所,尤其对女性而言。在勒若看来,专注性表现的是私人生活,而剧场性则是公共的一面。
描绘少女时期的儿童文学的女主人公总是在专注性与剧场性之间挣扎。如在玛丽·考登·克拉克的《莎剧女主角的少女时期》一书中,十几位女主角始终在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寻找平衡。她们在他人的观察下长大,永远位于舞台之上,渴望有所表演,同时又被期待要眼睛低垂。
“书本”与“剧场”的内在矛盾在一代代女孩的成长中冲撞着,直到近代才慢慢得以解决。《小妇人》中的乔·马齐开始能够专心在图书馆看书,又出入剧院,即使作者还是惩罚了她去剧院的行为——她最珍视的文稿因此被烧。从被侵犯的对象,到在专注与剧场之间盘桓的女孩,再到书本与戏剧都能同时兼顾的女性角色,描写少女时代的童书探索了两个多世纪。勒若也提到了现在最受欢迎的读物《哈利·波特》,认为赫敏集合了三个世纪以来书本中的女孩形象。而在电影《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中,当布莱克因为赫敏的才智从监狱里逃脱时,他没有如书中的描述转向哈利说:“你——不愧是父亲的儿子,哈利。”而是转向赫敏称赞道:“你真的是你这个年纪里最聪明的女巫。” 女性成就的荣光就这样代替父子亲缘的肯定,成为戏剧的中心角色。
文学奖与儿童文学的生产机制
19世纪末,美国已经有了近200多所公共图书馆,致力于社区儿童教育。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它们的作用不弱于教室。图书馆不仅教育孩子如何读书,也培养基本的公民素养。
因为长期承载的儿童教育功能,儿童文学同图书馆之间发展出了一种特殊关系,图书馆负责许多儿童文学奖项的颁发,其中最重要的奖项便是1921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建议为年度最佳童书设置的奖项——纽伯瑞奖。这些童书奖项极大影响着童书的评判标准。
实际上,从古代雅典人在公元前6世纪设立戏剧比赛起,各类文学都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奖项。然而,20世纪早期,新的变化出现了。诺贝尔奖1901年首次颁奖,不仅奖励学科成就,也定义了学科本身。评论家詹姆斯·英格利希提出,诺贝尔奖加快了早期大工业家的生产过程,奖项文化随着工业文化的兴起而生。它让人们产生一种观念,即竞争是这个世界的法则,这是工业企业家的精神结果。
纽伯瑞奖以一位书商和出版商——约翰·纽伯瑞的名字来命名,似乎也是这一精神结果的结晶,它暗示了人们给予儿童文学的支持是含有经济考量的。实际上它确实是在资本和商业的时代逐渐壮大,即使在它的描述和评判标准设定中,“文学”和“文学品质”始终是关键词,但这里的文学品质并不代表有着社会改革目标的文学。所谓的文学品质同图书馆精神密不可分,指的是“清晰、准确、有条理”,典型的代表如房龙《人类的故事》,记录着旅行冒险,人类英雄的丰功伟绩。儿童文学也受此影响,一年一年将风格巩固了下去,往往充斥着奇闻逸事、清晰的判断力和精确的时间线。
这些文本就这样被家长们选择,被孩子们阅读,它们有些被遗忘在历史中,有的成为集体的童年记忆。儿童文学便如此在家庭生活、教育环境,以及出版业与商人的复杂影响下塑造着一代代人。这些作品将故事带入孩子们的生活,影响他们未来的足迹。正如弗朗西斯科·斯巴福德在《小书痴》中写道,“那些令人转变的阅读经历。有时候,一本书进入我们恰好准备好的心灵,就像一颗籽晶落入过饱和溶液中,忽然间,我们就变了。”(徐鲁青)